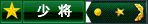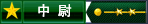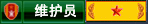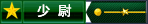刀起穗落,人车鼎沸。
收割的工作面上谁也不甘落后,谁也不能落后。运输车顶在屁股后面,谁落后了就意味着阻碍车子的进程,进程快的人向车上送筐的距离就加长,耗费的时间和气力加大。连长站在车上督战,大声提示着“XX班,加快进度”,“XXX,不要掉队”,若实在不行,他就亲自操刀,帮你割下几筐,助推一把。刚开始体力好的时候,我们班的进度不错,越往后就感到吃力了。高粱地的深处密不透风,体温被扎紧袖口裤管禁锢着,无法释放,汗水和药水被体温和阳光蒸烤着让人有中难以承受的感觉。一声声汽车喇叭越来越近,我知道离开掉队线不远了。为跟上进度,顾不得动作要领,只能拼命的挥刀砍穗,再挥刀再砍穗……
在我庆幸离开汽车喇叭声音远了一点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高举的镰刀带着高粱穗顺势而下的时候,镰刀下突然冒出了个草帽,我没有半点反应的时间,只听见“哎呀”一声,刀尖砍破草帽,直达头骨。
我慌了,顿时不知所措的呆站在原地,双手不由自主的颤抖着,脑子反复闪现着刀下那个似乎看见白色骨头的口子,带血的刀尖,带血的高粱……周围收割的场面依然如旧,所有的人都还在忙着各自手里的活,该死的运输车还在不停的用喇叭催促着进度,被砍的那个人还在从地上托举起装满高粱穗的筐子送上了车厢。等他拎着空筐子回到我面前的时候,草帽下一张挂满了血水和汗水的脸告诉我,受伤的是童祖勋!
我想说对不起,我想叫卫生员,我想让他下去休息,可还没开口他就说了三个字“班长哎……”随即就像没事一样又投入了抢收。这三个字是责备?是提醒?还是受伤后的疼痛的呻吟?当时没有时间给你想那么多,也不允许你想那么多。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一直干到了地头,趁着卫生员给他处理了伤口的时候,我递上一小段自认为是好吃的有甜味的高粱杆,自责的心才算有了点减轻。
几十年后再见面,我真想去摸摸童祖勋头上是否留下了刀疤,想去问问他是否记恨用镰刀砍他的班长,端起酒杯的一瞬间我改了主意,让那一刀,让那受伤后的痛,让那自责的难过统统化在酒里吧。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sv103160_副本.jpg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4-6-13 9:47:22编辑过]

 Post By:2014/6/12 18:39:26
Post By:2014/6/12 18:39:26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4/6/12 20:23:46
Post By:2014/6/12 20:23:46




 Post By:2014/6/12 20:32:18
Post By:2014/6/12 20:32:18




 Post By:2014/6/12 21:27:52
Post By:2014/6/12 21:27: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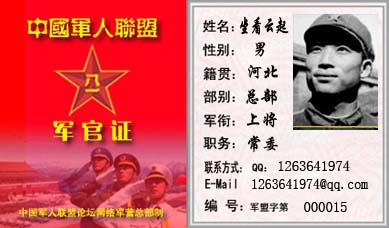


 Post By:2014/6/13 5:31:49
Post By:2014/6/13 5:31:49


 Post By:2014/6/13 5:57:16
Post By:2014/6/13 5:57:16




 Post By:2014/6/13 7:54:19
Post By:2014/6/13 7:54:19


 Post By:2014/6/13 8:27:04
Post By:2014/6/13 8:27:04




 Post By:2014/6/13 22:08:21
Post By:2014/6/13 22:08:21


 Post By:2014/6/14 8:09:52
Post By:2014/6/14 8:0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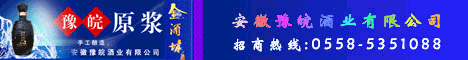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sv103160_副本.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sv103160_副本.jpg





 又一部《高粱红了》,主角:童祖勋。人物形象高大,故事情节感人,深赞!
又一部《高粱红了》,主角:童祖勋。人物形象高大,故事情节感人,深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