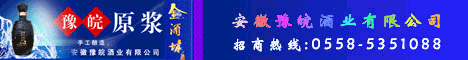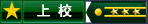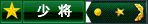第二十六回 一代人 舞翩翩多才多艺
俩兄妹 情切切无怨无悔
邱志鹏一出医院大门,就被陶丽娜带的一大帮人——‘红代会’的宣传队员们拦住了。
“你往哪里去?告诉你,你和我被抽去‘三代会’宣传队了!马上该我们演出了,赶快跟我走吧!”陶丽娜说。
“我有事……”邱志鹏还想冲出人群,早被有备而来的‘战友们’团团围住。
“还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陶丽娜这回不让步,一把挽住了邱志鹏的手臂,“走吧,马上要轮到我俩的独唱了!”
邱志鹏的男高音‘沁园春—雪’和陶丽娜的女高音‘白毛女—北风吹’是‘红代会’宣传队经典的传统节目,这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
连拉带拽,邱志鹏被簇拥进了县城唯一的那座影剧院。
影剧院里乌烟瘴气,人声嘈杂。长条椅被拉得杂乱无章,人们随意在上面蹲着站着,很少有人坐。到是椅靠上坐了不少人,也不管后面的人看见看不见。
舞台上灰尘扑扑。一连串好几个节目——‘拿起笔做刀枪’、‘亚非拉人民要解放’、‘起来吧黑人兄弟’、‘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的歌舞,把舞台上的木地板跺得“咚咚”响,演员们仿佛是在云雾中表演。
直到报幕员先后报出邱志鹏和陶丽娜的独唱,台下才略微静了些。
照样是满堂喝彩,照样是掌声口哨声不绝而耳。邱志鹏没有往常那样兴奋,而陶丽娜却格外来劲,又接着唱了‘见了你们格外亲’、‘谁不说咱家乡好’。
邱志鹏想,可惜没有笛子伴奏,陶丽娜的‘白毛女—北风吹’唱段前面要是有芦生的笛子引奏,效果会更好。邱志鹏知道,芦生的笛子吹得特好,在学校的几次演出中,他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很受欢迎。那颤音,那滑音,那单吐双吐,着实使人着迷。
明天一定要把介绍信开过去,把芦生的伤治好!他答应过的事是一定要努力办好的,何况是在芦花面前。邱志鹏的心思又回到芦生芦花那边……
天亮了,芦花被走廊上来往的脚步声吵醒了,发现自己是伏在哥哥的膝盖上。她揉了揉惺忪的眼睛,仰脸望着芦生说:“哥,你昨晚睡着了吗?你身上还疼不?”
“还好,不怎么疼。我也睡了一觉。”也许是昨天一整天太累了,虽然肩膀一阵阵作痛,但最后他还是睡着了。
“我们怎么办哪?”芦花说,“现在,我们口袋里布靠布,一分钱也没有……”
“走,到病房去,看看余洪水还要不要冰棒箱。把那箱子退了,不就有钱啦!”芦生拉起芦花,“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他强打起精神,看着妹妹蹙着眉,满脸愁云的样子,不由心里一阵阵酸楚,他佯装笑脸安慰。
刚走到病房门外,就听一位护士在发什么人的脾气——
“你这个人真是,小便也不起身,又不是起不得床的重病人!”
走进去,只见赤脚医生立在一病床边,满怀歉意地对那女护士说:“对不起,他是重病号,昨晚还昏迷不醒。”
“我看不象,他半夜还闹着要上街。”护士说。
赤脚医生被说得哑口无言。
“怎么回事?”芦生问。
“你看看,这床单被渥得透湿!没见过这么懒的人,小便不下床。真不害躁!”护士指着地下的白床单和棉垫絮说。
任凭周围的人怎么说,那余洪水拉着床单盖着脸,身子躺在光溜溜的钢丝床上。
“我不管了,你们自己给他铺床吧!”一赌气,那护士扭身走了。
一时间,几个人无所适从。
“我来吧。余、余队长,你起来一下。我来把你的床铺好。”犹豫一会,芦花走近余洪水的病床前,小声说。
“老子不住这个鸟院啦!老子现在就走!”忽然,余洪水‘哗’地一声掀掉床单,坐起身,随手摘掉头上的冷敷袋,从床上跳下来。他赤膊短裤,吓得芦花直往后躲。仔细看去,余洪水头还没有完全消肿,那眼睛眯成一条线。
喧闹声,吵醒了邻床的一位病人。“唉……”那病人坐起声,摘下口罩。
芦生看清楚了,原来是他们学校的数学老师郝林。
“郝老师,你怎么也在住院?”芦生问。
“哦,我的嘴时常发炎。现在学校停课了,没有教学任务,我刚好彻底治治。”
原来,自从那次被贴了膏药,因青霉素紧缺,没有彻底消炎。郝林的嘴就时好时坏。
“这位同志,刚才那护士有情可原。我们病人起码要尊重人家的劳动。”郝林转脸对余洪水说。
余洪水眯着眼睛看了郝林半天,“你是谁?反动学术权威!你以为我不认识你!你也有发言权?!”
“余洪水,你别这样。你起来,让我妹妹给你铺一下床吧!”芦生说。
“我是什么人?!贫下中农、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专政队队长!凭什么在这里受窝囊气!?不就是在床上洒了一泡尿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余洪水吊颈鬼倒发犟,“不用铺床了,我现在就走!”
“这怎么行!医生还没有发话,你不能出院!你的头肿得这么厉害,这样回去,我也不好交代!”赤脚医生一把抱住余洪水。
芦生打开棒冰箱,见里面还有许多没用完的棒冰,转脸问赤脚医生说,“还要冷敷吗?”
“嗯,医生没叫停。”赤脚医生说。
“那就继续用吧!”芦生说着,用不疼的手捡起余洪水丢在地上的冷敷袋,交给赤脚医生,“你再捣些冰块,继续给他敷吧。”。
“请你们不要多管闲事!我的命硬得很!我要走,我的事我自己作主,不需要你们为我负责,为我操心!”余洪水还在那里喋喋不休。
芦花实在是听不下去,脸气得通红,说:“哎!我说余、余队长,我们是多管闲事吗?你知道你昨天是什么样子,今天又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你冷敷用的冰渣是哪里来的吗?你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做什么的吗?你知道这装棒冰的箱子是是哪里来的吗?是我哥哥用六块……”
“芦花!”芦生用眼神制止了发‘连珠炮’的芦花。
“真是好心讨不到好报……”芦花嘟囔着。
芦生转脸对余洪水说,“你这样回去,头浮眼肿,怎么见你的老娘!你难道要让你老娘为你操心?为你伤心?!”
一听此话,余洪水开始焉了,坐在床沿埋下头。
“芦花,你替他铺吧。”芦生指了指地上的棉垫絮和床单说。
芦花眼里噙满了眼泪,默默地为余洪水整理床铺。那余洪水很不情愿地挪了挪屁股。
芦花三下五除二,把床铺好。扭身跑出去,一屁股坐在门边,把头埋在胳膊肘弯里,无声地咽哽起来。她又气又急,心里好委屈,不明白哥哥为什么要这样宽宏大量,这样迁就一个蛮不讲理、不知好歹的人!

 Post By:2010/12/11 21:23:52
Post By:2010/12/11 21:23:52




 Post By:2010/12/11 21:25:02
Post By:2010/12/11 21:25:02




 Post By:2010/12/12 9:12:32
Post By:2010/12/12 9:12:32




 Post By:2010/12/12 15:35:10
Post By:2010/12/12 15:35:10




 Post By:2010/12/12 19:06:58
Post By:2010/12/12 19:06:58




 Post By:2010/12/12 19:08:27
Post By:2010/12/12 19:08:27




 Post By:2010/12/12 19:09:39
Post By:2010/12/12 19:09:39




 Post By:2010/12/12 23:18:35
Post By:2010/12/12 23:18:35




 Post By:2010/12/13 14:15:19
Post By:2010/12/13 14:15:19




 Post By:2010/12/13 14:16:30
Post By:2010/12/13 14: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