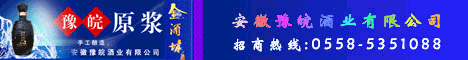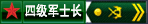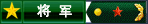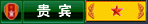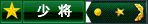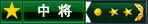声明:没当过兵,却一直对军人有着浓厚的感情,在下不才,却一直在努力耕耘着文字这片土地……
前沿哨兵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夜,故事的主人公,是四个卑微到不能再卑微的小人物……
这是阵地前沿的前沿。在前沿哨所的山洞里,住着我和来子,洞很小,仅容两个人,越南那边一道沟口的山坡上,有个越军的前沿哨,垒得象棺材盖,里面装着两个越南兵。
每天,当我们出洞,下崖,巡逻时,那边的越南兵也抄枪出动,四个人一字排开,从山沟这头走到那头,……他们一个是三十多岁的老兵,脸精瘦腊黄,腮上布满丝丝缕缕的血筋,一个看去不过十六岁,比老兵矮一头,一张圆脸粉里透红,眼睛总骨噜,肥嘟嘟一双大耳朵。我和来子给他俩起了外号,背后把老兵叫着“腔子”,把小兵叫着“嘟噜”。
巡逻渐渐引出了小把戏,四个人走着走着,不知是谁带头故意把对方往一边挤,挤着挤着四个人就都走到沟的对方二分之一地盘上,然后对方又往这边挤……没有任何上级的指示,这四个人总是不知不觉站成齐刷的一排,也不用任何人发出号令,一起迈右腿,一起迈左腿。有一次“嘟噜”迈错了腿,像倒线似的还紧倒两步取齐。见我看他,小圆脸立刻绯红,羞答答低下头半晌,活像出操时走错了步被人发现,怪难为情……
巡逻过后,就是互相的监视坚守。
那天,巡逻到狭窄的沟口,我们倚在石壁上休息,在相距不到十米的地方,两个老越也在他们那边的石壁倚着,来子掏出“中华”,“腔子”也摸烟叼在嘴上(“嘟噜”恐怕不会吸烟,因为从未见他抽过烟),然后就浑身上下乱翻……显然他没带火柴。
我瞥了他一眼,就掏出我那电子打火机,在手心一掂,手腕一翻,喀嚓打着,为来子和自己把烟点燃,极惬意地深吸一口……
“腔子”眼睛一亮,撂下枪起身朝我们移动了脚步……我向来子眨眨眼,微微一笑,把打火机喀嚓喀嚓连打十几下,通红的火苗儿好不鲜活……“腔子”的两眼都发蓝了,“嘟噜”却要拦他,只见他把“嘟噜”一搡,几乎朝我们扑来,却又猛地停住……
“喂,当兵的,点个火……”
“腔子”意外流利地说了中国语。
“嘟噜”紧跟他身后,圆脸涨成个西红柿,红中透青,两手紧紧把着枪……
我和来子一愣,互相使了个眼色。我就漫不经心走近“腔子”,举着打火机朝他伸直了胳膊……“腔子”嘿嘿干笑一声,要接,我没给,而是喀嚓把火打着,他又尴尬地笑,叼烟低头凑过时,我缩回了胳膊……
“腔子”没了笑意,满面恼怒。
我却拿出“中华”,连打火机一并递他。
“腔子”一见,立刻转怒为喜,说着“谢谢”,伸手就要接。那“嘟噜”却说了句不知什么,伸手挡住了“腔子”的胳膊。“腔子”把他狠狠一扇,一推帽子,歪头摆出副一百个不在乎的老兵架儿,伸手接过烟,凑近我打着的打火机点燃,眯着眼吸了一口。
“咋样?比你们的烟强多了吧?”我问。
“这烟,我抽过。”他有点不服气,但还是掏出烟盒--他们那种常见的大绿包--把未点的那支烟精心装了回去。
来子嘿嘿笑。他是没胆量也不愿意做这种“小淘气”的。我在用眼神徵求他的意见,他的默许使我决计再继续这难得的“娱乐”。
“你这烟,我抽过。”“腔子”仍不服气地重复。
“当然,”我一眼看到他脚上的大头翻毛皮靴和“嘟噜”脚上的“解放鞋”,
我指划着又说,“当然,你们见过世面,你脚上这双鞋,老美的,没错。他穿的那双鞋是我们给的……你们仓库里准还有法国货。你们准还得了老俄的什么玩艺儿?”
“腔子”狠狠瞪我,迸出一句:“我们越南人……能打仗……”
“哈,”我也故意歪头抖着一条腿作出兵痞状,“瞧你,一颗炮**弹飞过来,炸不到你,也把你这副骨头架子震散了。瞧他……刚不吃奶吧,那玩艺儿……你明白吧,怕还没长毛呢,……”
来子笑出了声。
“腔子”精瘦腊黄的脸涨红了,他斜起眼瞪我,一口紧一口吸烟。
“嘟噜”满脸惊骇,滚圆的鼻子尖顶着一层细密的滚圆的汗珠。
“腔子”终于把烟吸完,突然把烟头一扔,摘下帽子也一扔,捋起袖子瞪眼问我:“咱摔跤!”
我看一眼来子,他冲我挤眼。
“摔就摔!”我说着,就要摘下身上的枪。
旁边,“嘟噜”却一步冲过,横在我和“腔子”中间,最可恨的是,他的枪不再横在胸前,而是平端着直对着我,“腔子”又去推他,却没推动,他沙哑着向“腔子”喊了句什么,枪端得更平……
“算了,算了……”来子笑咪咪走过,拉住了跃跃欲试的我,冲“腔子”伸出小姆指摇摇,笑着冲紧张万状的“嘟噜”一瞥,他对“腔子”说:“算了,你看你这个搭档,连开玩笑都不懂,他任屁不懂!”
“对,不摔了,”我也就势为自己找到了台阶,“他任屁不懂!”
“腔子”恼火得呼呼喘气。“嘟噜”却仍朝我们平端着枪,指头紧扣着扳机,
端立不动。“腔子”捡起帽子,啪啪在腿上抽打,拎起枪大步就往他们的哨所走去,……走出几步,怒冲冲向还站在那里有些惊慌的“嘟噜”大喊了一句,是喊“嘟噜”随他回去,也不排除狠狠地骂了他一句什么,……
于是,我就和来子又倚在石壁上,点起烟,轻松悠闲地哼……
“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阿哥心忧愁……”
这晚上,只听他两个时而大声时而小声地吵了半夜,想来“腔子”很为白天没能够和我摔上一跤,心里极觉得别扭。
我和来子,却觉得少有的惬意。我说:“来哥,那俩口子可不如咱,他们怕是说要‘打离婚’了,他们是‘捆绑夫妻’,……”
来子说:“你就坏吧!非得让烂裆烂掉你这邪性劲头,你就老实了。”
可能,“嘟噜”让“腔子”骂惨了,一连几日,巡逻时疲疲沓沓随在“腔子”
旁边,连正眼儿也不敢瞅我们。
“腔子”挺来神儿,不知从哪儿也弄来个打火机,也是电子的,走到沟口就掏出喀吧喀吧打个没完,极为得意。
“‘腔子’是在向咱们示威。”我说。
“哼,他也是闲得难受。”来子说。
于是,巡逻时,我故意高抬腿猛甩臂,脚底下喀喀响,带起一阵风,瞅空朝“腔子”伸出小姆指晃晃,用脚在地下划个圈儿,吐口唾沫,用脚尖一点……
“腔子”和“嘟噜”莫名其妙。
“真有你的,连穿开裆裤小孩玩的‘哑巴禅’都想起来了,你尽是绝活儿……”
“他们懂吗?”
“谁知道!”
……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中午。
这天,我们俩刚下崖头,忽见“腔子”吱溜钻出他们的“棺材盖”,手里举个水壶踉踉跄跄朝我们奔来,“嘟噜”紧随他,慌张失措。
我俩急忙拦去,扑面一股酒气。
“腔子”被“嘟噜”拽个趑趄,站住了。他的瘦脸通红,脖子通红,举起那水壶冲我们喊:“中国兵,喝好酒,我们的……喝完,咱摔跤,越南人,中国人……”
来子用眼色制止我和他对峙。
我就冲“腔子”笑着说:“等你醒酒了再说吧,你喝成这样,就是我胜了,也像是欺负你。”
“腔子”用死鬼样的眼色瞪我,他把水壶凑到鼻尖下闻闻,又直瞪瞪朝我递过:“喝!当兵的,喝……”
我没接,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腔子”嘿嘿笑了,越笑越紧笑出了眼泪,他笑着,佝偻了腰,又咕咚喝了一口,他喝呛了,撕心裂肺好顿咳嗽,鼻涕眼泪,他抹了一把甩了,身子一晃,“嘟噜”要扶他,被他拼命搡开,又晃着水壶朝我和来子凑近。
“嘟噜”的脸在阳光下发白。
“当兵的……打仗,喝酒才是当兵的……喝酒……喝,当兵的……”
他叫着,把衣服一把拽开,露出洗衣板样道道骨头的胸脯,他又笑了,笑得凄惶笑得鄙夷,笑得寒气森人……
“当兵的,酒都不敢喝,还打仗?喝吧,酒……酒里没毒……喝,喝呀……”
“腔子”伸水壶的手在抖,他越凑越近,笑着,嘴在咧,却有大颗的泪珠涌出……
“都是当兵的,打仗,喝……”
他含混的声音无端带着哭腔儿。
我心里也在莫名地打战。我看来子,他眯着眼咬紧嘴唇肃穆地看着那水壶。
“喝……”
看着“腔子”手里的水壶,我觉它在无限膨胀,那死寂的黑绿色几乎浓雾一样挡住了眼前的一切塞满了这狭窄的山沟,一种同为小人物的卑贱感挤得我耳朵嗡嗡响像有人捏紧了我的脖子使我喘不上气……
我又看了眼来子,他并不看我。我狠喘一口,朝水壶伸去手……
“腔子”乐了,无声,但看出是真乐。
突然,“嘟噜”一步跃过,用枪猛地挑开水壶,水壶从“腔子”手里挑飞,一道暗绿的弧形,无声地落到沟底沙地上,眼前一片纷飞的晶莹,壶口流出道小溪,泊泊几声,小溪断流,干涸了,满沟酒气……
我早一步退到来子身边,不知来子怎么想的,竟伸手扶了我一把,好像我喝了酒喝多了就要醉倒……倒是“腔子”,只这么一愣,便嗷地一声长嗥,伸手揪住了“嘟噜”,没听“嘟噜”出声,已被“腔子”拽倒在地,醉了的“腔子”好一把干劲,只见他拽着“嘟噜”的腰带把他提起半人高,狠狠朝地下摔去,几下摔过,他抬脚把“嘟噜”踢得在地下打滚,“嘟噜”架不住他的美式大皮鞋,连声惨叫,“腔子”却不顾一切,夺过“嘟噜”的枪,用枪托劈头盖脑朝他打去……
“嘟噜”滚着躲了,这下子,“腔子”气疯了,他血红着眼睛哇哇叫着,竟不顾一切追上,一脚踩在“嘟噜”肚子上,死命要把他踏住。
“嘟噜”哇地哭了!
他的声音是孩子的童音,绝对童音!
我见来子的脸变得煞白,就在“腔子”又疯子般抡起枪朝“嘟噜”砸下之际,他箭一般蹿过,拼命托住了“腔子”手里的枪……
“还不快跑,等他打死你呀,……”
口鼻流血,被打懵的“嘟噜”惊惶失措地爬起身,竟下意识地朝我们这方跑来。
我和来子正全力想制服“腔子”。突然,“哒哒哒”,一阵惊人的枪声震荡了
山谷。
是“腔子”在肆虐中扣动了枪机。
枪声震惊了我,也震惊了来子,他把“腔子”一搡推倒在地,拉起我就往后跑。
枪声震惊了“嘟噜”,他冷丁停住脚步,茫然地去摸枪,却忘了枪在“腔子”
手里。
枪声震惊了“腔子”,他不再发疯,一屁股呆呆跌在地下,枪口有缕没散尽的青烟。
当我和来子擦身跑过“嘟噜”的瞬间,不知两边的大山上是哪方迫不及待地开了枪。
枪声呼啸着在我们的头顶。
跑回洞里,步话机里排长喊得正急:“来子,有我们掩护,紧急撤离,紧
急……”
来子抓着步话机,半晌,才答:“是!”
枪声更密更响。
“走吧!”
我俩出了洞,却谁也不想跑,只是一步步走向洞侧荆丛榛棵中的小路。我什么也听不到,只听到阵阵童音的哭声,我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眼前一片忽明忽暗的黑绿……
“有人哭!”来子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去,沟底已经沉积起一层二尺多厚的硝烟,天是晌睛的,万里无云,满世界似乎毫无声响,沟底,“腔子”还抱着枪木雕泥塑样坐着,旁边,站着重又跑回他身边的“嘟噜”,站得笔直……
他们被沉积着的硝烟层层覆盖。
“是‘嘟噜’哭吧?”来子问我。
我细听,却只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

 Post By:2010/8/21 7:55:17
Post By:2010/8/21 7:55:17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0/8/21 10:32:26
Post By:2010/8/21 10:32:26




 Post By:2010/8/21 10:56:32
Post By:2010/8/21 10:56: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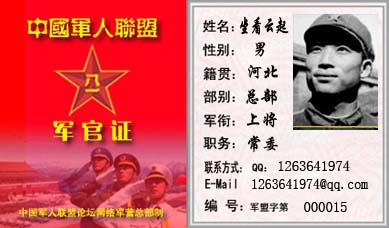


 Post By:2010/8/21 11:23:50
Post By:2010/8/21 11:23:50




 Post By:2010/8/21 14:05:50
Post By:2010/8/21 14:05:50




 Post By:2010/8/21 15:41:51
Post By:2010/8/21 15:41:51




 Post By:2010/8/21 17:16:14
Post By:2010/8/21 17:16:14




 Post By:2010/8/21 17:48:20
Post By:2010/8/21 17:48:20




 Post By:2010/8/21 21:40:50
Post By:2010/8/21 21:40:50


 Post By:2010/8/22 7:14:23
Post By:2010/8/22 7: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