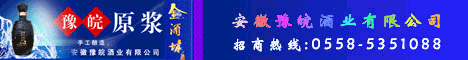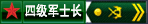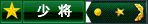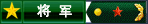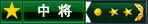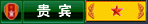难忘那段童年“军旅”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曾有这样的梦想:参加解放军。
在我幼小的印象中,军人就是勇敢,坚毅的代名词,无所畏惧又英姿飒爽。那个时候,很流行军装和军帽,特别是军帽上鲜艳夺目的红五星更是我们追捧的对象。要是谁家当兵的小子回乡探亲,我们一大帮伙伴屁颠屁颠地跟在别人身后,缠着他讲部队生活,那分景仰,比现在的年轻人崇拜“超女”要狂热得多。回忆我的童年,也因有了军旅之梦,而显得丰富多彩,更加难忘。
自打记事起,就跟随比我大的玩伴满山遍野的打游击。后来,我又靠手中《小李飞刀》、《燕子李三》、《董存瑞炸碉堡》等炙手可热的小人书,赢得小伙伴的拥戴,成为“孩子王”。领着一群野孩子上山打鸟,下池摸鱼,践踏菜园,偷摘瓜果。稍大,不想落为“草寇”,将十多个顽童“整编”为解放军独立团,我自封为团长,众伙伴依照个头或年龄,任命为营长,连长,排长、众皆提拔,没有兵。此后一段时间,“张营长”、“李连长”地在村里村外叫开了,皆大欢喜。
既然是“部队”,属于“武装”力量,不能没有“武器”。制造武器,有一个艰难的发展阶段。那个时候没啥玩具,于是自力更生。首先是配备宝剑,各自将家里的木块偷出来,集中在一起按照小人书上宝剑、大刀的样子制作。而后背着父母翻箱倒柜偷出仅有的红布,绑在剑柄。成天刀剑不离身。放学兴致时,舞动刀剑劈下去,哪家的高粱、油菜就会遭受摧残。自从被不认识的张大爷抓住现形后,就发现刀剑太大,易于暴露。终就放马南山,刀剑入库。
此后,又削木为枪,射击时“啪”的一声,姿势到位,音效靠嘴。这是拥有枪的发展创新阶段。
经过“技术改革”,武器也有了进步,学会了制造有枪身、枪管、击针,而且还有一定威力的“洋火枪”:用铁丝掐成一个枪的轮廓,再翻出昔日到处淘弄的被烧掉底火帽的弹壳,将其绑在枪口位置,再把在学校偷取的窗钩掐去弯处,做成击针,用橡皮筋带动击针。弹壳尾端放入火柴磷硝做成的底火,再扣动扳机。那一段时间,村落里时不时就响起“清脆”的枪声。再后来,发展成在弹壳里塞上鞭炮药,细石子等,发出的声音比雨**管还响。记得曾有一次,由于鞭炮药放得过多,抠动扳机,只听“轰隆”一声响,弹壳被炸掉半截,而且还振得院落里鸡飞狗跳,两个连长和一个排长被声响吓哭了。当大人从屋里跳出来看时,我们都呆呆地站在院坝边上。一顿训斥责骂后,便下令,任何人不准在弹壳里放鞭炮药,否则以“违抗军令罪就地正法”。
“部队”有了武器,一切就有了规章,独立团也比较正规。当然,也有走狗、汉奸、叛徒“分子”。部下经常报告,张排长又向老师出卖了“独立团”,李连长又投靠某某某了。为清理叛徒,学着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动作,用枪逼着不听从指挥的“叛徒”,说上一句“你这个叛徒,我代表党和人民枪毙你。”而后“砰”的一声,将其推到在地,有板有眼,煞是郑重。
当“独立团”发展到不止“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时候,这种游戏也就失去了新鲜和刺激。恰在那时,邻村小孩子组建“游击队”,招兵买马,实力一天天壮大,对我“独立团”多有挑衅,双方擦枪走火,摩擦也不断升级。
战争缘于我方张连长与对方“游击队长”课桌之争。那时,时值小学三年级,他俩一桌,课桌中央刻着“三八线”。彼此约定互不侵犯。可是张连长自恃我方在班上人多势众,总是有意无意越界侵夺,对方忍无可忍,几次“照会”“谈判”后,传来“战书”,择日一决雌雄。
为了显示“我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战前,我方做了积极的战前动员和战术研究,具体“剿匪”方案是:我方将部队埋伏在对方进入主战场的路上,设下埋伏,攻其不备。那一仗,交火甚烈,以至于双方拼红了眼,小规模地使用了“土块”,树枝等“杀伤性武器”,导致违背“战争公约”的动作出现。那一役,我独立团大获全胜。而对方,多数是哭着撤离战场。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胜利的喜悦很快在母亲的扫帚下化为疼痛。那些流着鼻血,头顶青包的“败将”回到家中,家人问:谁打的?回答:XX的部队。于是我作为战犯被押解到我母亲和“败将”父母组成的“军事法庭”,判决书的核心内容是我放大了人民的内部矛盾,造成了无辜的流血事件。除了无情的扫帚,我母亲为平民愤,还口口声声要将我“正法”,我的辩护词是:我作为指挥员,曾试图化干戈为玉帛,但萌生此念时,我已经控制不了局势……
经此一役,“独立团”解体。随着年龄的增大,识字的增多,我开始接触《敌后武工队》、《地雷战》、《地道战》等战争题材小说,将对军营的热爱融入阅读之中。
二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似水童年,那段难忘的“军旅”就会浮现在眼前。现如今,那颗“军旅”的种子已经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Post By:2010/8/8 0:11:25
Post By:2010/8/8 0:11:25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0/8/8 8:37:51
Post By:2010/8/8 8:37:51




 Post By:2010/8/8 9:02:56
Post By:2010/8/8 9:02:56


 Post By:2010/8/8 10:59:13
Post By:2010/8/8 10:59:13




 Post By:2010/8/8 12:32:39
Post By:2010/8/8 12:32:39


 Post By:2010/8/8 12:48:10
Post By:2010/8/8 12:48:10




 Post By:2010/8/8 15:00:05
Post By:2010/8/8 15:00:05




 Post By:2010/8/8 15:09:30
Post By:2010/8/8 15:0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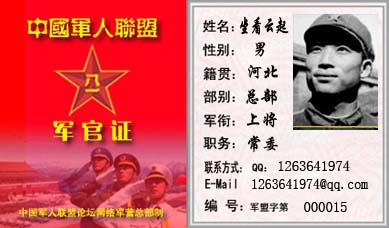


 Post By:2010/8/8 20:11:25
Post By:2010/8/8 20:11:25




 Post By:2010/8/8 20:22:19
Post By:2010/8/8 20:2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