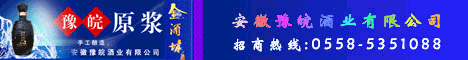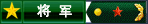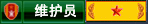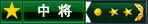第三十回
干姊妹 喜相逢泪雨滂沱
亲母女 共枕眠耳语呢喃
德圆在茅屋顶上做了个‘悟空望月’的姿势,高喊着:“苇香——来人啰!有人向你姑妈家走来啰——”
“你在上面喊魂吧!赶快铺芦苇,天黑前不把漏补好,看我怎样治你!”茅屋下面不见人影,只听人声。
“真的,你们出来看,好像是芦生他们回来了!”
从茅屋里走出两个女人,是苇香和江婶。她俩踮起脚向通向江堤的田间小路望去——“是呀是呀,是芦生和芦花!呃?怎么还有两个当兵的?”苇香眼尖,“姑妈,你看是不是还有两个当兵的跟在他们后面?”
“是不是那个人武部政委的儿子?”江婶问。
“不像。”苇香说。
不远处的田间小路上,缓慢地走着四个人。雨后的泥泞小路,使他(她)们走起来歪歪斜斜,慢慢腾腾。走近了才看清楚——是芦花搀扶着芦生,后面两个军人,一男一女。
“妈——我们回来了啦!”芦花发出清脆的叫喊声,刚到茅屋门前,就扑进江婶的怀抱。
“我的儿,你们可回来了!”江婶一把搂住她的两个伢,“可把我急死啦!”她轻轻抚摸着芦生吊着绷带的手“这——”
“妈,我的手没有大问题,医生说两三个月就会好。”芦生笑着说。
“妈,这么多天,你一个人在家不热闹吧?”芦花笑吟吟地说,“我们俩可想你呢!”
“傻丫头,这几天,有你表姐做伴,我怎么不热闹?就是着急你们!”江婶把芦花的头贴在自己脸上,“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何况你们是去看病。”
“妈,我们走到天边都不在乎。这世上好人多着呢!刚才过江前,有人还让我们挣了不少钱呢!你知道吗?我——”芦花越说越有劲。
“好了好了,留着话慢慢谈。这里还有远路来的客人呐!”苇香见一家人只顾自己亲热,,把另外两个军人冷落在一边,打岔说。
见一家人那样亲热,那女军人不知是喜是悲,禁不住抹起眼泪来。她转过身,仔细端详着这破茅屋,嘴里喃喃地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忽然,从茅屋上跳下一个光头人,陡然站在那女军人面前,吓了她一大跳。那光头人嘻嘻哈哈地说:“女施主,想不到什么?是想不到小孤山的和尚不在寺庙里打坐,而在这茅屋顶上练轻功吧?”
女军人还没有缓过神来,那光头人又接着说:“女施主,你是来小孤山进香的吧?我可又有事干啦!阿弥陀佛——”他做了一个出家人最习惯的动作。
“德圆,你又在出什么洋相?”苇香过来,刚想伸手拧德圆的耳朵,那和尚却一溜烟跑了。
“解放军同志,你别见怪,这小和尚是个活宝,他人不坏。”苇香说。
正说着,那位年轻的男军官把江婶拉到女军人面前,和霭可亲地说:“大婶,你认识她吗?”
江婶站在女军人面前,仔细端详起来。看了半天,摆摆头,揉揉眼,又看了看说:“嗯,面熟,面熟,一时想不起来。”
那女军人脸上微笑着,眼眶里却饱含着泪水,见江婶认不出自己,就把军帽摘下来,把刘海摞向一边,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渐渐地,眼眶里的泪水禁不住慢慢地溢了出来。
“你仔细看看,看看她像不像十七年前你在江心洲芦苇荡见过的人?”那年轻军人还在开导。
“你、你、你就是那国民党的太太?你是姚、姚兰!?”江婶如梦初醒,颤抖的手伸向女军人,“天哪!你、你真的来接芦花啦?!”
听到这儿,那女军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哗哗’淌,她“哇——”地一声扑在江婶身上“姐!我的好姐姐呀——”两个女人就紧紧搂在一起,抱头大哭起来……
“我的好姊妹,你可真的来啦!你可让我好等哪!”江婶一边抹眼泪一边擤鼻涕,“我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啦!”
“你记得吗?我说的,只要我不死,我就一定要来接我们的女儿!”那姚兰说。
“怎么,你们,你和你丈夫,齐、齐什么来着……”
“齐凯。”
“对,齐凯!你和齐凯没、没有去台湾?”江婶诧异地问。
一听此话,那姚兰破涕为笑:“姐,我的好姐姐!你真糊涂呀!”
那年轻的军官更是笑得前俯后仰,“大婶,只怪我,上次来没有讲清楚。我们齐部长和姚科长当时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就是明的是假国民党,暗的是真共产党,怎么会跑到台湾去呢?”
“哦——都怪那顶大檐帽,让我真假不辨,好歹不分啦!”
“哈哈哈——”
“咯咯咯——”
破茅屋前响起经久不息的笑声……
一阵悲喜交加,那姚兰当即吩咐张干事立即赶赴孤山镇,连夜拍电报,告知军区后勤部齐凯部长:一,女儿芦花已找到;二,立即寄六百元钱来,帮助江婶盖瓦房;三,办理芦花的油粮户口关系,把她的户口立即转到南京。
“事不宜迟,你趁天还没黑,赶快去吧!今晚你就在孤山镇找个旅馆住吧。”她对张干事说。
“那,你呢?”张干事问。
“我就在这茅屋里将就一夜吧。”
“这里条件太……”张干事望了望破旧的茅屋,欲言又止。
“我女儿在这里住了十七年了,我住几天算什么!何况,我女儿还没有正式认我这个妈呢!”姚兰笑着说。
张干事从手提箱里拿出一个手电筒,准备出发。
德圆说:“我也去,我去带路。”
苇香说:“我也去,我回娘家。”
三个人就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了。
是夜,昏暗的煤油灯光里,一张旧床上睡着三个女人。江婶有意让芦花睡在姚兰一起,共着枕头,使她娘儿俩能唠唠贴心话。
“叫我,叫我妈。”姚兰搂着芦花柔嫩的腰肢,附在她耳边,轻声细语。
“嗯……好痒。”芦花羞涩地扒开姚兰的手,紧闭着眼,把头偏向一边。在这个陌生亲妈妈面前,她显得格外不自然。
姚兰双手捧过芦花的脸说:“花,你长得可像你爸爸呢,比你妹妹还像!”
“什么?妹妹。”脸转过来了,眼还闭着。
“对,你还有个妹妹。”
“她叫啥名?”
“叫海燕,比你小一岁半。”
“名字好洋气。”
“你的名字也好,是你爸爸取的。”
“不是吧?是我妈妈取的吧?因为我哥哥叫芦生,所以我就叫芦花。我和我哥是共一条苦根长大的。”终于,芦花睁开了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
“不管是谁取的,反正芦花这名字很好听。”
“呃,南京城大不大?”
“大,好大,你去了就知道了。”
“从小妈妈就对我和哥哥说,等我们长大了,有出息了,一定要带她去芜湖南京见见世面。”昏暗的灯光里,芦花忽闪着大眼珠。
“死丫头,你叫妈了没有?”床那头,江婶朝芦花的屁股踹了一脚。
“呃,等过了中秋节,你带我妈和我哥去南京玩一趟,好吗?”那芦花不理睬江婶的话,对脸贴脸这个亲妈,她不是不叫,只是一时叫不出口。
“好!南京可好玩呢,有高楼大厦,有宽阔的马路,有成排的法国梧桐,还有长江大桥。有中山陵,雨花台,玄武湖,好多好多好玩的地方,让你哥哥和你妈玩个够好吗?”姚兰一一介绍。
“呃,你家住在哪儿?”芦花问。
“什么你家?死丫头,还不叫妈妈?”江婶又踹了芦花一脚。
“妈妈,你别打岔嘛!”
“花,什么你家?”姚兰说,“是你是我是我们的家。告诉你吧,我们家在南京市鼓楼区天山路二十四号。我们家可好呢——地势高,空气好,看得远。有阳台,有庭院,有冬青树,有花台,有葡萄架……”她忽然压低声调说,“告诉你,我们家大门口还有解放军战士日夜站岗放哨呢!等你回家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呃,你男人,哦——是我爸,是多大的官哪?”
“不管官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
“你做他堂客,怪享福的哦!”
姚兰‘噗嗤’一笑,“傻丫头,什么男人堂客,以后到了南京,不许说这些乡下话,难听死啦!”说着,就把芦花紧紧搂在怀里。
那芦花就任凭她搂着,紧闭着眼睛,再也不言语了。
三更时分,姚兰醒来,她怀里不见了人。坐起身,却发现芦花在床那头,搂着江婶,睡得正香。

 Post By:2016/1/1 7:17:36
Post By:2016/1/1 7:17:36


 Post By:2016/1/4 11:01:45
Post By:2016/1/4 11:01:45




 Post By:2016/1/5 10:07:54
Post By:2016/1/5 10:07:54




 Post By:2016/1/6 12:40:24
Post By:2016/1/6 12:40:24




 Post By:2016/1/7 5:57:32
Post By:2016/1/7 5:57:32


 Post By:2016/1/7 5:59:04
Post By:2016/1/7 5:59:04




 Post By:2016/1/8 9:17:22
Post By:2016/1/8 9:17:22




 Post By:2016/1/8 16:18:38
Post By:2016/1/8 16:18:38




 Post By:2016/1/10 11:03:02
Post By:2016/1/10 11:03:02




 Post By:2016/1/11 7:08:46
Post By:2016/1/11 7: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