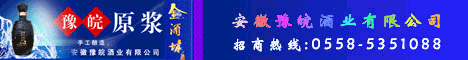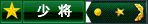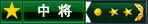我与两位建国战友(下)
我和阿芦是一个连的战友——660团指挥连,同时也是师、团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队友,在团业余文艺宣传队他是演员,我是乐手和编剧。阿芦的表演路子很宽,文武兼备,这在业余文艺宣传队里是难得的人才。尤其是他的武场翻跟头,一般人一次只能做1-2个小翻,而阿芦由于身材好加上平时刻苦练习,一次能做三个以上的漂亮的小翻,每逢阿芦出场,几个跟头一翻,台下立马掌声雷动。提起在宣传队的日子,我与阿芦还有过一次过命的经历,说来话长。
记得那是660团第二期宣传队,我和阿芦、太阳不下山、刘孺子牛、半瓶醋、李先玉、贺杏成、李宝成、夏仲领、史其军、还有两个65年的老兵吴炳干和张金合住在大礼堂西边的耳房里,阿卢和我睡的是上下铺。那年冬天天气特别的冷,为了取暖和烧开水,上级给宣传队每个房间安装了一个带烟囱的老式煤炉,炉子装在房子的中间,两边是我们的高低床,用铁皮筒连接起来的烟囱从床前平行天花板悬空通向窗外。那时候还没有蜂窝煤,烧的是原煤,煤气特别重,我们一边捡煤块烧,一边把碎煤和泥做成煤饼或煤球放在炉子上烤干备用,晚上临睡前还要用煤泥封炉保火,如果封的不好,熄火了,第二天就要重新起火升炉,起火升炉是件复杂的事情:首先要把炉子与烟囱分离搬到户外,清空炉膛,然后在炉膛里放上报纸或柴草,点燃起底火,再加放劈柴,为了旺火有时候还要往劈柴上浇泼点煤油或柴油,等劈柴烧到一定的火候再往上面加煤块,在加煤的同时还要不停的对着炉门煽风,加好煤炭,立马在炉口上安个拔火筒,直到煤炭发火。按程序,这绝不是一个人能够同时完成的,所以每次起火升炉大家都自动聚到一起,围着炉子,劈柴的劈柴,点火的点火,浇油的浇油,煽风的煽风,你一言我一语的,嘻嘻哈哈,既热闹又开心。
可能是因为多次重新起火升炉,炉子经常退下安上的,造成烟囱接头松动留下的隐患,已记不清是那天夜里了,我们入睡以后,悬架在天花下面的铁皮筒烟囱不知什么时候开断了,天寒地冻,门窗都关的紧紧的,大家白天排练了一天,晚上都睡的呼呼的,尽管室内煤气弥漫,谁也没有感觉到毒气的危害,直到快天亮,幸好睡在门口下铺的68年沭阳老兵李先玉内急起来解手,发现情况不对,赶紧把大家喊醒,打开门窗,穿上棉大衣,相互搀扶,撤到室外,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煤气中毒,学名也叫一氧化碳中毒.初期感觉为头痛、头昏、恶心、呕吐、软弱无力,严重时迅速发生抽痉、昏迷,如不及时救治,很快呼吸抑制而死亡。可怕的是煤气这东西往往人清醒的处在其中而意识不到,等意识到已经中毒了,更何况我们那次是发生在熟睡之中,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事后体检,整个宿舍十几个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煤气中毒,可能是热气上升的缘故,睡在上铺的阿芦、太阳不下山、夏仲领、史其军、贺杏成、李宝成等人都相对重的多,最重的要数阿芦和贺杏成,因为他们的上铺在中间,两头都不靠窗户,密不透风,当时人已经站不稳,是大家把他们从床上背到室外的。今年淮安聚会我们拉呱到宣传队的时候,我问阿芦还记不记得那次煤气中毒了,他说咋不记得呢,那是过命的事,终身难忘啊。经我这么一问,阿芦的话夹子一下子打开了:幸亏李先玉战友及时发现,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忘不了那天一大早,大家挨排坐在大礼堂前,迎着初升的朝阳,吐故纳新,呼吸新鲜空气;忘不了卫生队的战友们及时送来氧气袋和药品;忘不了炊事班的战友们送来香喷喷的病号饭,忘不了战友们相互搀扶沿着指挥连门前的小鱼塘遛弯散步,恢复体力;忘不了……忘不了……
悠悠岁月,冲不淡那人那事之精彩,千言万语,道不尽友情之珍贵。忘不了啊,这就是大卢、阿(二)芦和我的故事——两个战友一样名,三个兄弟一般亲 。
感谢淡泊立志战友指正。 哈哈,好友相处,习惯亲呼其名而隐其姓,久而久之对方名字是那几个字也就不去管他了。那些年我只知LU、LU的喊,还真的没有注意到卢和芦,音同字不同,实在抱歉。
由于时间久远,很多人和事已经记的不是很清晰了,本文涉及的战友较多,若有不敬之处,请战友们海涵,下次相聚,定当敬酒致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5-8-16 14:57:44编辑过]

 Post By:2015/8/16 10:53:34
Post By:2015/8/16 10:53:34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5/8/16 12:01:54
Post By:2015/8/16 12:0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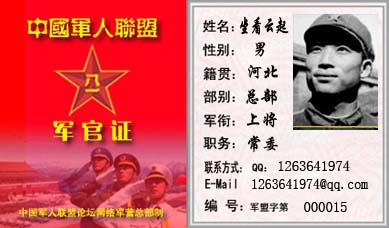


 Post By:2015/8/16 12:32:14
Post By:2015/8/16 12:32:14


 Post By:2015/8/16 15:18:25
Post By:2015/8/16 15:18:25




 Post By:2015/8/16 15:33:54
Post By:2015/8/16 15:33:54




 Post By:2015/8/16 16:51:02
Post By:2015/8/16 16:51:02


 Post By:2015/8/16 18:41:43
Post By:2015/8/16 18:41:43




 Post By:2015/8/16 19:08:58
Post By:2015/8/16 19:08:58




 Post By:2015/8/16 21:16:17
Post By:2015/8/16 21:16:17


 Post By:2015/8/17 5:48:55
Post By:2015/8/17 5:4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