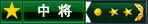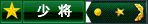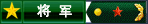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微信图片_003.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微信图片_003.jpg

夕阳西下,汽车在山路上艰难地爬行。驾驶员说今天还算顺利,估计到达济南汽车站的时间应该在下午五点左右。
就快到济南了,我脑海里极力回忆着大舅的模样,可就是想不起什么样。他会来接我吗?学校在哪里?行李怎么办?望着山峦中的夕阳,心中不由生出一阵惆怅。
下午五点多钟,一路颠簸的汽车,终于疲惫地停在了济南长途汽车站。
大舅,大舅呢?我趴着车窗往外看,下了车又四处寻,可没有发现大舅的身影。等了好一阵子,还是没见他来。
旅客渐渐散去,汽车也开走了,空旷的车站只剩下了我和车长。
“说好了大舅来接的。”我不停地自言自语,有埋怨,也有委屈。
车长一边不停地看表,一边不时瞅瞅远方的公交车站点,同时还不停地安慰我:“别急,我和你一起等。”
我看车长不时地用眼光瞟着对过的公交车站点,知道他还要再坐公交车才能赶回部队。就装着突然发现了大舅,指着远处说,“来了,大舅来了。”
车长一听很高兴:“真的吗?”
我指着远处一个人说:“真的,那不是吗。”
车长长舒一口气:“太好了,我也得去坐公交了,这是最后一班车了,再见了,小同志。”说罢,他冲我做了个鬼脸,飞快向公交车站跑去……
天完全黑了,大舅依然没有出现。
喧闹的大街上渐渐冷清,行人越来越少。我扛着沉沉的行李,漫无目的地徘徊在车站附近。委屈、恐惧、疲惫和无助一下子涌上心头,把背包一扔,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掩面而泣……
突然,透过泪眼,我看到一双鞋,是解放军特有的绿黄色胶鞋。我抬起头,看到车长正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你大舅没来是吧?”
我点点头,泪水再次滚了出来。
车长便对我说:“真是猜对了,幸亏我没走。”说罢,他挨着我坐下,揽着我的肩膀:“没事,别怕,叔叔送你。”
“叔叔,你怎么还没走啊?你怎么办啊?”
“我没事,我是军人,是你的车长,我要把你安全送到学校。哎,对了,你学校叫什么名字,有报到证吗?”
我赶紧从包里拿出入学通知书。车长接过去,看了一眼,然后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有这个就好办了。”
他走到路灯下面,再次确认了报到证上的地址,然后对我说:“你别动,就在这里等我。”说着便向不远处的一辆三轮车跑去……
不一会儿,一辆三轮车从马路对面迎着我而来。车还没停稳,车长就从三轮车上跳下来,对我说:“呵,你们学校在济南东郊,离这儿还真不近哩。上车吧,车钱我已经付给师傅了。”
我急忙拿出钱往他手里塞,他拦着我说:“算了吧,车长替你付了,只是我不能亲自送你去学校了,熄灯前我必须赶回部队。”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转身到车后面,蹲在地上,查看了三轮车的车牌号,又掏出钢笔把号码记下来。
蹬三轮的师傅笑着说:“解放军同志,你是对我不放心啊。”
车长笑了:“嘿嘿,我是他的车长,我得保证他的安全啊。师傅,拜托您了。”说罢,他用立正的站姿,给师傅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三轮师傅连连点头:“解放军同志您请放心,我保证安全把他送到。”随即启动了三轮车。
我感激地跟车长道别,路灯下的他微笑着,不停地向我挥手,直到他在我的视线里消失……
“解放军,车长……”我心里不停地默念着,突然想起:“嗨!我还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三轮车师傅没有辜负车长的期待,不但把我送到了学校,还扛着行李把我送进宿舍,交给了丁排长——我的另一位负责军训的解放军手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位影响我一生的沂蒙籍解放军叔叔、如同我人生中的一盏明灯,不仅照耀着我,也潜移默化着我。在他的影响下,我不敢不做好人。有一年我坐在沂河桥墩上钓鱼,先是听到头顶上划过一声绝望的喊叫,随之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擦着头皮飞过,随后“扑通“坠入桥墩下面的激流里……没待我反应过来,从水里忽地冒出一个人头,是个女的,她脸上全是血,绝望地瞪着两眼,高举双手叫唤两声,又沉入水中,然后再没了动静。
我脑子起先一阵空白,但很快意识到出事儿了。我水性并不好,但不能坐着不动,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我扔了鱼竿儿,脱掉雨衣,纵身跳进水里,激流一下子把我冲出老远……
寻找中,我突然碰到了她,她也抓住了我。
被她抓住的一刹那,我的头脑里竟然还快速地闪过几个“救人”招数,如“从背后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打晕”等等,但是现实情况却是毫无作用。她死死抓着我,抓着我跟她一起往下沉……
求生的欲念让我用尽全力想带她脱离旋涡,但湍急的水流让我身不由己——我觉得就要不行了,突然却一下踩到一个圆硬的金属圈儿,这是她的自行车。在她和自行车冲进河里的时候,由于惯性,车头扎进泥沙里,车尾部分翘得好高,我这一脚正好蹬在了后轮上。
真是命不该绝,借着这个支撑,脚下使劲一蹬,稀里糊涂拽着她离开了深水流子,接着又狗刨式地划拉几下,竟然踩到了坚实的沙地。(后来我多次想,“脚踏实地”对于落水者意味着什么)
这时,大桥上已经围满了人,看到我们脱离危险,纷纷鼓掌。大家七手八脚过来帮忙,把我们两个拖上大桥。这时,我才看清落水人,是位年龄不大的姑娘。
本不好意思提这件事儿,但这件事儿,却跟我遇到的那位好心解放军车长血脉相承。没有他的影响,我做善事的由头儿,不会那么明确,没养成帮人一把的好习惯,遇到那样的场景,我也不一定不眨眼睛就往河里跳……
只是那位车长,你还记得我吗?你现在又在哪儿?论年龄也应该在65岁上下了,早已复员,甚至退休了吧?多么期待还能见到您,甚至为此还做过梦,梦中的你冲我笑着:“小兄弟,你得请我看戏啊。”
最后,需要多赘一句的是,后来才知道当工程师的大舅,他当时援外,被单位派到了科威特,回单位后才看见父亲寄给他的信和电报,多年来大舅一直为这事后悔不迭。
薛 岩
2019年3月10日星期日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微信图片_004.jpg


 Post By:2019/12/3 14:05:03
Post By:2019/12/3 14:05:03




 Post By:2019/12/3 14:07:50
Post By:2019/12/3 14:07:50




 Post By:2019/12/3 14:11:50
Post By:2019/12/3 14:11:50




 Post By:2019/12/3 16:07:35
Post By:2019/12/3 16:07: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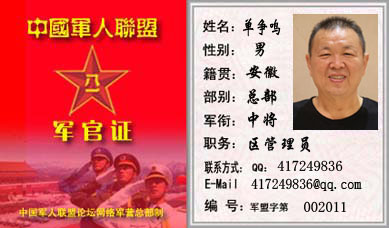


 Post By:2019/12/3 16:40:30
Post By:2019/12/3 16:40:30




 Post By:2019/12/3 18:12:25
Post By:2019/12/3 18:12:25




 Post By:2019/12/3 19:40:25
Post By:2019/12/3 19:40:25




 Post By:2019/12/3 20:36:03
Post By:2019/12/3 20:36:03


 Post By:2019/12/4 9:47:16
Post By:2019/12/4 9:47:16




 Post By:2019/12/4 9:49:10
Post By:2019/12/4 9:4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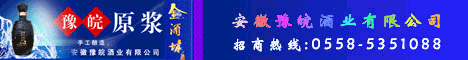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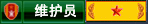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微信图片_001.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微信图片_00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