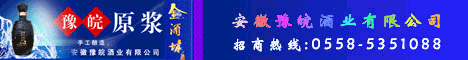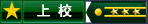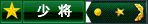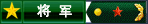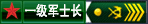我的班长 (五)
——忘不了那人那事征文
那时候,连队总是把最重要、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有线三班,在班长的带领下,我们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没有吃不了的苦。
泗湾湖架电线,从金湖县开始,一根根水泥杆,没有起吊设备,总是班长自己一马当先,硬是用肩膀扛用铁锨用木杆顶,插进土洞里竖起立正。
在小刘庄通信连的小农场,旱改水,班长硬是把自己当牛做马,犁地耙田,弓着腰,让粗粗的麻绳通过肩膀,像纤夫一样拉着,走在犁耙前面,而让我们在后面扶把手。一个月下来,终于把盐碱地改成了水田。
营房电话线路出了故障,不管风霜雨雪,烈日寒夜,班长总是一声不吭,拿起登高板,找到故障电线杆,几步蹬上去,修复线路,直到通话正常。
班长像一个铁汉子,高大身躯从来没有弯过腰,也从来没有叫一声苦。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偶然听见班长在轻轻地呻吟……
这样的班长,任何战士跟着他,都会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在所不辞!
记得那是我入伍的第二个年头,家里来信,说部队来人到我乡下葛家老屋,到我毕业的高中,到我们街道调查我的情况,家里问我是不是在部队犯了错误。我很是奇怪,我在部队,在班长的带领下,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啊。
左思右想,说不定是在调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我是红卫兵头目,曾经批斗过县里头号‘走资派’,我们还去小孤山扫过四旧。
一个多星期,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惶惶不安。这天,连队要我去排文娱节目。活动室里,许多天没有见过的付东升副指导员让我做‘导演’。
那是排我写的一个三句半,我让连卫生员打鼓说第一句,哪知道这位姓王的71年新兵不听指挥,非要打锣说最后半句,我好说歹说,他就是像老话说的——‘要你打鼓你非要打锣,要你上山你非要下河’。
这几天,我心情本来就烦躁,就不耐烦地说:“嘿,你怎么不听调啦!?你不就是个新兵……”‘蛋子’没有说出口。
哪知道这位卫生员根本不买我的账,大声说:“你算个球?!你在师宣传队女兵面前出风头出惯了,跑到我们连队也想出风头?!”
嘿,他们连队,把我当外人!他可能是指我在舞台前为女兵独唱伴奏手风琴——那女兵贺素霞是演李铁梅的,《春光万里红旗杨》也唱得倍儿棒。每当这个节目,她总是习惯性朝我微笑点头,示意我可以开始拉过门了。
我感觉,这个新兵心理有些扭曲,本不想与他计较,但是连队交给我的任务不得不完成啊,就把鼓硬往他手上按,哪知道,他把鼓往乒乓球桌上一丢,就是不干。我急了,问副指导员:“副指导员,你管不管?”
副指导员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那位卫生员就大声骂起来—— “管你妈逼!”
这下我忍耐不住了,当红卫兵时,老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一个新兵蛋子,竟敢如此猖狂,骂我的老娘!骂我可以,骂我的老娘不行!我上前,一把拽住他的手,问:“你骂谁的妈?!”
“就是骂你!怎么?想打架?!”他用挑衅的目光盯着我。
这时候,我脑子发涨,感觉血一个劲往头上涌,我揪住他的胸部,咬牙切齿地说:“你以为我不敢揍你?!”
“打人啦!葛文凤打人啊——”他竟先声夺人。
忍无可忍,神差鬼役,我一拳打过去,顿时,他门牙流血了!
我知道我闯下大祸了!果不其然,连长施国华立即找我,狠尅了我一顿,说我动机是好的,打人说什么都是错,“哪有这样做思想工作的?!”连长说着,拿出一个笔记本,翻了几下,又合上,“算了,不给你看了……”。
晚上,连队集合,指导员点名批评我,要我写检讨,以观后效。
熄灯后,班长拽着我来到老地方,还没等我坐下,一拳打在我胸口,我仰面朝天跌坐在地下,只听他大声嚷:“日小妈!你、葛文凤脑子是进水了还是吃了火药?怎么这样不争气?!”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哭过,这次,我眼泪汪汪,一肚子委屈只得向我的班长、我的兄长罗学友倾诉,我伏在他膝盖上,真的好伤心。
“从我记事起,我妈就起早摸黑帮人洗衣服,供我念书,他竟然骂我妈……”
好大一会,班长拍着我的背说:“都怪我!有些情况,我没有提前告诉你,没有提前让你写入党申请书……”
“我不够格,不敢写……比起你,我永远不够格……”
第二天,我离开了连队,离开了我的班长,开始了我‘老兵游子’的所谓文艺兵的军旅生涯。
而我的同学老乡盛唐,本是一株‘瘦’苗,在通信连这个肥沃的土壤里,茁壮成长,当上报话班长,后来,又当上了文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5-6-25 18:49:05编辑过]

 Post By:2015/6/25 12:59:28
Post By:2015/6/25 12:59:28




 Post By:2015/6/25 13:19:56
Post By:2015/6/25 13:19:56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5/6/25 14:16:12
Post By:2015/6/25 14:16:12


 Post By:2015/6/25 15:40:59
Post By:2015/6/25 15:40:59


 Post By:2015/6/25 15:41:32
Post By:2015/6/25 15:41:32


 Post By:2015/6/25 17:48:57
Post By:2015/6/25 17:48:57




 Post By:2015/6/25 19:45:46
Post By:2015/6/25 19:45:46




 Post By:2015/6/25 19:57:18
Post By:2015/6/25 19:57:18


 Post By:2015/6/25 21:25:52
Post By:2015/6/25 21:25:52


 Post By:2015/6/25 21:33:28
Post By:2015/6/25 21:3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