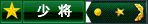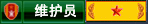1971年的春末夏初,连队从淮胜公社的老乡家里搬出,正式住进了泗湾湖农场的营房。营房是盖在灌溉渠的边上,三幢房子成“U”字形排列,两端分别是连部仓库(枪库)和后勤厨房, “U”字底部是一幢主要建筑,全连都住在这个房子里。在“U”字围起来的中间,是一块场地,是集合出操,吃饭活动的重要之地。这营房其实就是草棚,柱子、房梁用的是毛竹搭建起来的框架,棚顶覆盖着油毛毡,可以遮阳挡雨。从地面向上一米多用的是泥巴垒成的土墙,在土墙的上面再插上一排周边缠上稻草的芦苇把子,两面糊上泥巴做成了墙壁,墙壁上等距离的开上几个几十公分的口子,口子外面挂上一块用油毛毡和竹片扎起来的方块,下面用根竹竿一撑便成了窗户,可以采光通风。房子在靠墙的一边和中间的走道两侧,用土坯垒砌一排矮墩,铺板朝上一架就成了睡觉的床,两块铺板为一个单元,单元中间的是上下床的通道,毛竹杆上拉起一根铁丝,用来蚊帐。看上去简陋无比,可它都是我们亲手搭建起来,是千年以来泗湾湖里第一批称得上房子的建筑。住在这里面,看着整齐划一的“豆腐干”,漱口杯子里用一个角度向一个方向倾斜的牙刷,虽然有些发黄,但四个角都拉的倍直的毛巾,就有回到营房的感觉,它就是我们在泗湾湖里的家啊!
房子有了,田也整出来了,种点啥?眼看到了季节,连队还是没有接到任务,从农村来的兵也都猜测过,按照地域和环境当然是种水稻,但不仅大规模的插秧问题难以解决,就连育秧都还八字没有一撇呐,种水稻谈何容易?河北的战友多数认为种小麦、玉米和高粱,可当时的季节不对,时间也不允许在等下去。结果让我们傻眼了。农场下达的任务居然就是是种水稻,而且是用一种没有听说过的方式 —水直播。说白了,就是把稻种直接播到水田里,省去了育秧、插秧的环节,让稻种直接成长为水稻。听了技术人员的介绍,种过稻子的战士纷纷摇头,在他们的记忆中老祖宗就没有干过直播种稻的事,当兵的这样干,能行吗?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句军中名言在泗湾湖农场同样适用。于是平整的大田里就出现了像种麦子一样播种水稻的场景。十几台播种机,一字排开,几个壮汉拉着根绳,拖着装满稻种的机器在田里走。和围湖造田的挑担子比,这活既轻松又自在,就跟玩似的。很快营房周围的几十亩地全都播下了稻种,机耕队立马给田里灌上薄薄的一层水,在光合作用下,水里的稻种很快就发芽成长起来,没几天一片嫩绿便窜出水面,迎风摇摆起来。
转眼到了盛夏,太阳在没有一丝树荫的湖滩里,每天肆无忌惮的发着淫威,加上湖底泥土的含水量太大,稍微一晒,脚下的热浪就是滚滚而来。上晒下蒸酷暑难熬!“人在地上热的跳,稻在田里哈哈笑”永康的兵用这样的心理暗示来增强抵御暑热的能力,也被我一直记到了现在。
这样的天气对稻子的生长是好事情,对停放在露天里的车炮可不是好事,生锈发霉是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虽说我们身在泗湾湖,是第一批农场兵,但保持武器处于良好状态是当兵的最基本职责。因此车炮场日,保养武器,各连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放松。那天下午,应该是我当文书后的第一个车炮场日,按照计划,连队在去湖外的炮场擦完火炮后就带队回营房擦枪,考虑到室外温度太高,连长决定各班在各自的铺位上擦枪。我打开枪库的门,看着配备枪支的战友一个个拿枪出去,确定每支枪都有人保养后就和通讯员去擦手枪了。大家都知道,车炮场日里,时间是比较宽松的,只要抓紧擦完枪炮,剩下一点的时间能够自己安排。平静的车炮场日在值日排长的哨声响起后结束,我进枪库清点完数字,锁好门出来吃晚饭,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
晚饭后,天气变得很闷,很热,稍微一动就是大汗淋漓。熄灯哨吹过之后,操场上是一反常态,仍旧有三三两两的战士穿着短裤汗衫在谈心,有的还跑到制高点——排灌渠的坝子上找风。在极其难受的情况下,与其闷在油毛毡下的蚊帐里出汗,还不如在外面边吹风边喂蚊子。说起泗湾湖的蚊子,那可是厉害的很,特别是夜晚,叮起人来奇痒,为防蚊当时都涂抹一种驱蚊液,效果不错但副作用也不小,我曾经几次用涂完防蚊液的手握着钢笔写字,没多久光滑的笔杆上就出现了好多个坑坑洼洼的麻点,被防蚊液给腐蚀的不像样子。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少用为好。那天晚上在外面的人,几乎每人手里拿着一条毛巾,边谈心边甩动,像马尾巴似得,为的就是赶蚊子。低声的话语中不时伴着毛巾甩出来打在皮肤上“叭、叭”的声音,为寂静的湖滩夜空增添了不少的动感。可能是太热的缘故,原先钻在蚊帐里的人也陆续跑了出来,人数一多便惊动了连长。他站在场地中间,像喊口令似得,赶着大家回去睡觉。

 Post By:2014/7/30 18:36:31
Post By:2014/7/30 18:36:31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4/7/30 20:00:26
Post By:2014/7/30 20:00:26




 Post By:2014/7/30 20:25:52
Post By:2014/7/30 20:2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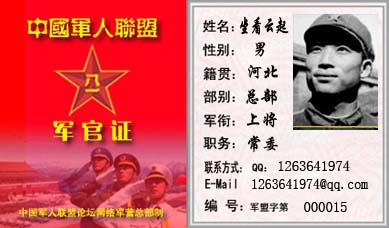


 Post By:2014/7/30 21:00:22
Post By:2014/7/30 21:00:22


 Post By:2014/7/30 21:04:06
Post By:2014/7/30 21:04:06




 Post By:2014/7/31 5:45:57
Post By:2014/7/31 5:45:57


 Post By:2014/7/31 6:01:39
Post By:2014/7/31 6:01:39


 Post By:2014/7/31 10:37:52
Post By:2014/7/31 10:37:52




 Post By:2014/7/31 16:05:32
Post By:2014/7/31 16:05: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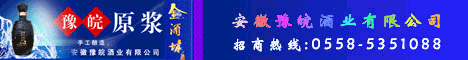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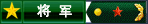


 应当看到思想政治工作做得还不到位;农药的管理制度也存在问题。
应当看到思想政治工作做得还不到位;农药的管理制度也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