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炮师长
● 成都军区 纪 莹
他的经历并不传奇。
从士兵到师长,中间一步没少。他也从来没想过缔造传奇。从技师到指挥员,他坚持以一种脚踏实地的方式转变并前行。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四川预备役高炮师师长陈志勇。
当然,他也有他的与众不同。
无论是当年的南部前线还是今天的预备役部队,无论是与电阻和螺丝打交道,还是统领部队,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对战争的忧患和思考。军人的职责就是为战争。但忧患和思考仅止步于“忧患和思考”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忧患和思考需要用实践来体现——在他三十五年的军旅生涯中,从技术人员走向指挥岗位,他不但带领部队全面发展,还身体力行不懈地进行科技创新。这种忧患和思考还需要成果来说明——历尽寒暑数载间,七次获得全军科技进步奖,极大地提升了战斗力;信息化研究成果达二十八项,都在演习训练、抢险救灾中得到了检验;探索的“组网饱和式打击”“夜间反空袭作战”等一批实战管用的战法,创造了七项高炮夜间训练纪录……他因此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六次,并被评选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他带领下的四川预备役高炮师被四总部表彰为“全军预备役部队建设先进单位”……
获得成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所有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一定少不了“坚持、累积、突破”。
探究陈志勇的这一行进方向,还是从战争开始吧。
从战争开始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当夜晚再一次如期而至时,地处南疆边境的小镇河口陷入了又一个暗夜。暗夜如同释放出无数黑色吸附离子似的紧裹着一切,包括所有平静与紧张。
陈志勇平静地盯着在黑暗中闪烁的雷达显示屏,全神贯注又心无旁骛。大战在即,身为高炮团的雷达技师,就是保证它们——高炮的“眼睛和耳朵”——雷达的正常、准确、无误,从而保证我们的侦察机安全,保证一旦有敌机威胁我们的领空,就毫不犹豫地锁定、指引导弹击落它。这是他的职责要求,也是他任务完成的标准。
荧光屏上的回波信号一闪一烁,在陈志勇眼里,这闪烁是稳重中带着自信,自信中又有点狡黠——人机之间某种默契的理解,往往是由人单方面决定的。
在几乎是不多不少的三年前,一九七六年二月,陈志勇入伍来到了这个团,而几乎又是从新兵开始,他就与这些机器打交道,就与这台雷达打交道,日积月累的磨合,不厌其烦的拆、装、维护、演练……不说是烂熟于心,也几乎了如指掌。支撑着这部雷达工作的电子元件上百万个。
曾经在一次参与大修时,陈志勇跟着厂家的技术人员,将拆卸下来的零件摆满库房一地,然后从中理出头绪组装复原——这不是出于好奇的自找麻烦,而是为了像庖丁解牛一样深入地了解它们,再或者,要于这了解中建立起一个信念——人的能力常常决定机器的性能。
说到性能,陈志勇手心沁出一层密密的细汗。汗水在他根本无意识的态度下分离出了一个紧张的他。我军雷达的历史只能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追溯。一九四九年我们从国民党军手里接管了一些美、日遗留的旧雷达,接着又补充了少量苏式旧雷达,从而蹒跚起步。此后又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了研发、生产。应该说,三十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在防空预警和几次小规模作战中也发挥了作用。而从中涌现出的雷达英雄更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陈志勇就是其中之一。
少年时,看到图画书、小人书上的雷达以及雷达兵,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羡慕,甚至是强烈的兴趣。到了部队,不但见到了真正的雷达,而且还要亲手、真真实实地操作它、维护它。从内心讲,陈志勇有点如愿以偿的满足。或者是出于这种兴趣和爱好吧,让他在这个岗位上发挥出了才干,也在这个岗位上从士兵成长为军官。
可又正是时间和经历,让他一想到性能就不由得捏了一把汗。他操作的这部即将执行作战任务的雷达,是我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苏联帮助下,仿制的警戒雷达。随着一九六○年苏联专家全部撤退之后,没有了技术支持以及零部件保障,仿制工作遭遇了很大损失和困难。
一九六○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国家方针,虽然大大推进了雷达工业前进,但随之而来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十年,也让人们心里都清楚我国科技的水平和生产力的迟滞。由此而产生的对雷达的担忧不是庸人自扰。
团里的雷达故障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几乎是一不留神,一不小心,雷达就黑了,就莫名其妙“闹情绪”了。大家时刻被这种无常折磨,有时候会折磨得冒火。一次一个性格急躁的老技师,满头大汗修理了半天,故障还是没排除,一气之下,他一边嚷着:“什么破玩意儿!”一边一巴掌拍在机器上。而这机器也像服了软似的,“嗞嗞”两声恢复了显示。从此以后,每每维护修理之前,这位技师就先来个下马威,重重地给上机器两掌。当然,可不是次次都灵验。
这在雷达站、甚至在全团里都传为笑谈。但笑声背后有太多笑不出的东西。
从凌晨到深夜,从深夜又将开始黎明,时钟不紧不慢,稳健地向发起进攻的时间行进。所有的人都满弓一样紧绷着,严阵以待。
陈志勇下意识地在衣服上蹭了一下手掌——几乎毫无察觉地、极迅速地擦了一下手心的汗,然后继续缓慢转动操作手柄——扫描、目标、方位、距离、锁定……一切就绪!
一切就绪!
当拽着弧光的炮**弹呼啸而出,火光映天如昼;撕开夜空般的隆隆声响,震得天摇地动;雷达显示屏上的信号急促而更加频繁地闪动,战前的一切静默和紧张像挣脱了蜡封的僵壳,剧烈变化——战争开始了。
战争就这么开始了。但在三十二年后陈志勇的记忆里,这个开始并不是界线分明的由一线划开。因为与战前漫长的准备相比,这个开始简直就是来不及捕捉的一瞬。开战后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也根本无暇将这个开始以里程碑的形式铭刻在记忆里;而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还在继续的战争不会让开始停顿。
在克服了最初的紧张之后,部队积累了经验,应对得越来越沉稳。但是对开战前的炮火准备和支援,也越来越倚重。不可否认,我们这支军队是历经战火考验而成长起来的,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毕竟一代人的革命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继往开来的道路上,荣誉代表不了未来。热带山岳丛林作战——对已在和平中度过了三十年的部队来说,有难度。虽然没有提枪背炮冲在最前线,没有面对面地与敌人厮杀,身在雷达站、善于思考的陈志勇已经有了一些对战争的看法,也许轮廓不甚清晰,但却让他萌生忧患:未来战争战线可能会越拉越长,在战争的初期阶段,敌我双方可能根本不会见面,却会感知——而且感知到对方比见面还多的信息、情报。这种感知需要的是更加先进的技术。
高炮部队是技术的产物,反过来说,对技术的依赖性比步兵更大。高炮防空作战的能力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战场感知能力上大大超过敌人。说回来,这种感知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和技术保障……
战场的隆隆声中,陈志勇感到自己手里雷达重如万钧——这些重要的感知实在是太重要了。
自开战后,他就睡不踏实,总担心雷达屏幕一片漆黑,总担心失去雷达的高炮成了仰天空叹的瞎炮。当然,这种重要,也不全是自我“加压”出来的,有时也是领导和战友们“逼”出来,“提”上去的。从新兵开始他就在业务上表现出了超人一等的素质。新兵第一年在全团比武中拔了头筹;在报务队集训时,很快他就是零差错,并以第一名的成绩结业。由于此,他被选派到昆明军区雷达修理所和石家庄军械学校学习了一年的雷达专业。回来后又肯于刻苦、乐于钻研,又因此而提干,可以不谦虚地说,他绝对称得上,工作实、业务强、技术精。
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或者说,有准备的人总是等待着考验的机会。
作战进行到了第七天,雷达非常争气地、大毛病没出地连续工作了七天。
这天,作战任务又将开始。正在工作的雷达荧光屏稳重地用闪烁继续分辨、扫描着——我方作战飞机、敌方侦察飞机,几乎一丝可疑都逃不过它的“眼睛”。可突然的,雷达屏一个强闪,“刷”的黑了,全黑了!这个场景陈志勇脑子里设想过很多次,但当它成为现实摆在面前时,那一瞬间他也跟着刷了屏似的,脑子一片空白。何止他,在场的所有人都后背腾起一阵冷汗,脑子跟着雷达荧光屏一起黑了一下。
团长的电话在黑屏的即刻响起:怎么搞的!半个小时内必须修复,这是死命令!
战争不可能因为这里的故障而推迟。我们出错就等于走进了死亡的穴位,将胜利拱手相让!若此时敌机来袭——简直不堪设想!问题出在哪里?!——陈志勇的大脑已经迅速重启,快速运转了。
站长和全站的同志都在着急,都在担心,都在催促。
陈志勇冷静下来。非常冷静。他脑海里可能没有人的大脑结构图,但却有雷达完整的电路图。几个最容易出故障的地方被迅速排除后,陈志勇果断地说:“电阻,一定是电阻!”飞速拆下后挡板,在复杂密布的电路线里,陈志勇敏锐而准确地发现了出问题的电阻,又小心翼翼地将这细如发丝的电阻接上。
九分三十八秒。不过十分钟,雷达重新启动!
战后,团里为陈志勇报请二等战功。
三十二年前的这场战争,对陈志勇来说收获是很大的,当然,这种收获不仅是荣立的军功和和平年代难得的参战经历,而是好比“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于所处的位置,在战争的全局中,对技术战争有了更多置身其中的认识和体会,并成为他此后人生与军旅奋斗“诸元”中最活跃最核心的一个因子。
人生的“诸元”
战争结束后,陈志勇像当时大多数表现优异的军官一样,被送进宣化炮兵指挥学院深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他开始正式思考:军人的职业与追求的事业是什么关系?如果要担当责任,何以报国?理性的战争和战争的非理性,理论的战争和战争的实际,发展的战争以及未来的战争……
相同的问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思考的价值也是不同的。
陈志勇的父亲是位可以谈资格的老军人。一九四八年,父亲从甘肃山丹入伍,成为王震将军麾下一员,并随进军西北,参加了解放新疆。此时父亲已是连指导员,当然,或许还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优秀的。在陈志勇看来,父亲的优秀还体现在他对事业的忠诚和踏实。到了新疆后,部队改为屯垦军,为农四师,虽然架子、机构和作风还是军事化的,但从军旅意义讲,父亲已经结束了戎马生涯,将开始扎根新疆、建设新疆的新人生。
一九五二年,一个怀着建设祖国一腔热血的山东姑娘,从牟平到了新疆,成就了千里姻缘,她就是陈志勇的母亲。
一九六四年,陈志勇八岁,这一年随着他记忆启程的,是从地处大西北的新疆到了位于大西南的贵州。这次南下,亦是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
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开始后,当时为了加强三线建设中的政治工作,要在全国抽调两千名优秀干部,在新疆范围内计划了十个名额。陈志勇的父亲被选中,名列其中。于是举家搬迁到了贵州。
到了贵州后,父母亲分配在林业部门工作。这些部门都彻底远离了军事生活,但父辈对党的忠诚和踏实,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陈志勇。
一九七三年,高中毕业后,陈志勇沿着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的规定道路,到贵州龙里下乡当了名知青。
他们那批到龙里下乡的知青共有三个人,二男一女。这其中唯一的女性名叫邓黔珍,是陈志勇小学、初中、高中时的同学,并将随着漫长岁月又成为一起入伍的战友,继而又成为他相濡以沫的妻子。
这三位知青的到来,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广阔天地的新鲜生活,但乡间的农人可不这么看。
由于他们前辈大哥哥大姐姐们抑或天真、抑或无知、抑或可爱又可恨的行为,老乡们对他们不但失去了原有的新鲜和兴趣,而且还有很深的偏见,譬如,通常认定知青们不会干活,继而,只能好吃懒做,再发展下去,就是偷鸡摸粮……
陈志勇秉性里的东西是不会让自己顺着别人的偏见一路滑下去的。当时农村干活是挣工分,陈志勇不但起得早,而且毫不吝惜力气,没用多久,他的工分在生产队就是数一数二了。他的表现纠正了一些偏见,也得到了从村长到村民的公认。但是,当现实的利益摆在面前时,人心里的那台天平依旧是会失衡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招兵工作开始了。陈志勇报了名。在当时,他真的不知道想参军是不是因为骨子里的热爱。就如前面提到的,参军入伍也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可供选择的规定道路,而且是较为光明的一条。由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热爱,报过名后,他也就听之任之,继续下地干活去了。
村长对陈志勇报名多了个心眼。因为村长的儿子也正适龄,也已报名参军。招兵是有指标的,如果要在自己儿子和陈志勇之间做出选择,出于公心,村长觉得可能应该让陈志勇去,但出于私心,肯定是让自己的儿子去当兵找出路呀!不知道村长有没有为这件事纠结过、矛盾过、自我斗争过,但就后来所知道的事实是,村长把陈志勇的名字压在了村委会那张唯一的破桌子下面,而把自己儿子的名字报了上去。
听之任之的陈志勇无从知晓内情,也没太往心里去,该干吗干吗。
春节临近,陈志勇请假回家,在路上恰好碰到村长陪着来家访的接兵干部。陈志勇迎面打了招呼,正要继续走,接兵的连长喊住他,说,小伙子高高大大、精精神神的,怎么不报名参军呀?听这位接兵干部的口气,明显有着对陈志勇参军不积极、思想有问题的批评。
陈志勇一头雾水,愣愣地说,报了,早就报了呀。
村长一脸尴尬。
如果注定了人要走一条路,那么无论怎么拐弯,最终都能绕回去。
离开贵州龙里,踏上南去的列车。出了贵州,到了昆明;过了开远,换上“没有汽车跑得快”的小火车,陈志勇刚刚开始的军旅还在继续。
火车一路走走停停,沿途放下几位战友,而陈志勇依然向前。在边境还没有在他的脑子里形成概念时,火车终于停在了再不能向前开的边境——河口,陈志勇服役的地方到了——某军高炮团。
刚到团里时,团里对从知识青年来到部队的新兵,有与农人们异曲同工的偏见。但当某些化学效应以稳定的分子式构成后,一种表现就会成为一贯。陈志勇很快打破了大家的偏见,标志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团里的比武。
此时陈志勇入伍不过六个月,“新兵蛋子”的全称还正名副其实。但在比武中,他不但军事第一,而且在业务比赛中比团里资格最老的同志都熟练,考核成绩远远抛开别人成为第一。团长记住了他,对他印象又好又深刻。
入伍一年多,他入了党。两年多,他提了干。三年时,他参了战。战争结束,又有幸重回校园。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能引人深思的东西太多了。当然,这种深思还必然建立在如饥似渴的求知和阅读基础上。入校后,从雷达炮兵基础理论到各种科技知识,从战例战术到军事战略,从古今到中外的大量书籍都让陈志勇着迷。因为他从中感到了自己的欠缺,感到了急迫,还感到洞然新开的知识空间有如深潭般奥妙。探究这个空间让他感到新奇的同时,还因为此前的许多空白无知而惊讶。当时已有一些学术刊物对刚刚结束不久的战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它们从战术层面分析,认为我军军事理论陈旧,以落后装备与更落后的对手,在现代完成了一场低技术战争。这是他第一次冷静的、就像旁观者一样看待他亲身参与的这场战争。也许从感情上,他拒绝这个批评,但从理智上,不能不正视这个批评。特别是读到了一些关于外军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闪电空袭半小时后,出动地面部队,十天后胜利结束战斗。
一九七三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战略指导与作战上,广泛利用电子技术和使用各种战术导弹”。——高技术战争早已经横空而出,可看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在热带山丘丛林的战争,用的是总让人捏把汗的旧式雷达,发挥的还是人海战术。
下一场战争还这样继续吗?
未来我们永远是与比我落后的敌人较量?
未来的较量还可能以人海取胜吗?“剑不如人,剑法胜于人”的说法在可贵中含有多少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哪!
一年半的军校生活,扎扎实实的从实践到理论。由此路径,陈志勇将思维认识里定义的战争粉碎了之后,又牢固地进行了优化重组。而重组后,让陈志勇对战争有了更立体的看法,它不再是局限于雷达站一隅,而是多剖面多角度。理论还必须回到实践。军校毕业后,陈志勇回到了老部队。
战争与和平
战争不会太久,和平还会远吗?
一九八四年,南边边境战火又起。在两场战争的和平期间,陈志勇除了完成去军校深造,还完成了人生的另一件大事——结婚生子。
妻子与他一起离开插队的农村,一起入伍到部队。入伍后分到五十九医院当护士。一九七九年时,他们在不同的岗位参加了共同的战争。妻子提干比他早半年,不过总体来说,继青梅竹马之后,他们又续写着并肩前进。所以,战火再起时,他们将继续在不同的岗位参与同一场战争。
这时,陈志勇先是作为团司令部参谋,继而又以该团一营副营长的身份奔赴了前线。此刻,妻子所在的医院也为前线二线医院,赶赴了医疗救护的第一线。
战前,陈志勇写好了遗书。在遗书中,他以通达的常情和温情,安慰妻子要正确而平静地看待死亡、理解牺牲,并将自己珍视的一件崭新的军大衣作为如果牺牲后的遗物,留给出生不久的儿子,希望能温暖他的成长。
战前的这份无畏或伤情,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相比于五年前,他多了丈夫和父亲两个充满亲情牵挂的身份,而是这次战争,他将不以雷达技师的身份坚守在雷达站,而是要带领官兵到真正的血与火的第一线。
整个战场充斥着“战场”的味道。这味道是以焦煳为主混合着人的血与肉、石头与泥土、小草与大树。“硝烟”一词根本无法描述其中的复杂,抑或是硝烟的内涵实在丰富得让人难以捉摸。
陈志勇带着营里的干部战士,穿越无处不在的硝烟,从近六十度的陡坡向主峰爬去。
脚下的地是发烫的,经过二十六天的炮火准备,山上的蚂蚁都已经粉身碎骨。上山的路也因此而更滑,一步不实就会滑下去两步,负重上山更加重了下滑的危险。但陈志勇带领官兵必须克服危险,尽快把弹药送到前线。战争有多激烈,弹药就有多需要。
战争自凌晨打响,似乎就进入了白热化,并且迟迟都不降温。送上去的弹药就像抛进沸水里的冰块,消耗得快极了。可陈志勇他们不但要迅速将弹药送上去,还要安全将受伤的战友抬下来、把牺牲的战友背回来……时间好像在跟一切作对似的。陈志勇带着大家不知道连滚带爬上上下下来回了多少趟,只知道耳边的隆隆声没断过,只知道流下来的血很快就与炮灰溶成了比大地还深的颜色。当听到我们的红旗已经插到了边境主峰,枪声终于稀薄下来,他才就势躺在滚烫的大地上,抹了一把脸上的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水。
是的。这次战争,属于高炮部队的陈志勇并不是以防空作战的角色参与,而是被派往前线担负后方运输。这种十分辛苦而且很不幸运的任务,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原因。这次战争敌我双方都没有计划将战争升级到空中,防空领域更多的是以威慑与预警而存在。可是这种参与让陈志勇感觉,是上天在让他体验,体验最真实、最血腥、最残忍的战争。
炮**弹擦着头皮而过,活生生的战友说牺牲就牺牲了,抬着缺胳膊少腿的伤员和年轻的牺牲了的战友尸体,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这还不算最难受的,当听到战场上一些因信息不畅造成误伤时,他更是难过。一个穿插分队还没穿插到位,我方的炮击已经按预定时间开始,而这个分队又恰好进入我方炮火覆盖区……
就像炮兵有雷达可以感知一样,什么时候战争的每个环节都可以知己知彼的如同眼见为实?当然,陈志勇想得更多的还是雷达和高炮。通过这次置身战场,在学校曾读过的那篇批评文章又一次跳出来刺激了他。出于大的战略关照,这次高炮部队没有承担更多的任务,但下次呢?以色列的空中优势和中东其他国家防空力量的薄弱,在战前就已经给出了胜负答案。中东的几次战争已经向世界军事说明防空的极端重要,已经向防空力量薄弱的国家亮出了黄牌!
当然,此时的陈志勇囿于环境和身份,并无法将问题想得更深入,他的所想所感更多的是,血腥而猛烈的战争场面映照进他的脑海中的客观反映。这种重要就如古人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烽火台上的狼烟。而在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下,信息的传递因为难度又更增加了重要性。就像那个陷入我方炮火的分队……
战争中信息太重要了。技术进步是一个必然,那未来战争,对信息的要求依赖肯定会越来越大!怎么解决信息的问题?
陈志勇在硝烟未散的战场上的所思所想,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但却非常可贵,因为身在此山中,而唯有在山中,才会有“横看成林侧成峰”——就像打下了基础。尽管他当时并没刻意去梳理成熟、明晰条理,但却已经像种子一样,生了根,等待着条件适宜就会发芽成长。而且,忧患培养出的苗子比盲目乐观浇灌出的花朵,能够更强的生存。
战争再次告一段落。和平再度回到许多人的身边。
战后,陈志勇提升为营长。百万大裁军之后的一年,他又被选拔到军部,在军司令部炮兵指挥部任参谋。
从一九八六年三月到一九九六年三月,从正营到正团,他在这个位置整整任了十年参谋。这十年包含着,或者说,可以总结为两个“寓言”。
一个寓言是关于忠诚和踏实的穿透力。
来到军机关工作,陈志勇感到身边的老参谋机关经验丰富,业务熟练,而其中更不乏两次参战的佼佼者。所以陈志勇把自己放在虚心学习、努力充电的位置。
而且他觉得需要学习的空间也实在太大了。在作为技师与雷达打交道时,非常微观而具体,微观到一个电容,具体到一颗螺丝钉。在营里带兵时,具体而操心,要保证完成任务,还要保证干部战士从思想到人身的一切安全。而在机关工作,个人自由度大,但综合要求高。既要是所负责的业务的活字典,还要有指导这项业务的全局把握能力。也就是说,既要会施工,还要会设计,要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行家里手,还要有能够为机关首长当好参谋、甚至“越俎代庖”的运筹谋划能力。
陈志勇对自己从电阻和螺丝钉启程的道路是非常有自信的。但要将从细微到全面的这个跨度把握好,还是需要学习的。
机关工作锻炼人,同时也消磨人。忙于应付完事务工作,若稍稍一懈怠,就真是时光飞逝如电,徒留白头伤悲。而拉开架式地列出必读书目,制定学习计划,作出一副要自学成才的样子,时间上不允许,最终也往往落空。陈志勇恰恰又是那种不事声张的人,他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读一切有价值的书。
大家只知道陈志勇的业余时间比较多,因为他长年是“地域性单身汉”。说来也怪,结婚之前他俩倒两小无猜似的,常常在一起。可自从当兵以后,特别是结婚之后反倒严重的聚少离多。他在河口时,妻子在开远。他到开远没两年,妻子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双方年迈的父母转业回到了贵阳。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妻子的肩上——说实在的,他很是内疚,也很是感激妻子的付出。让他因此有了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光学、电子学、卫星遥测、雷达、通信等等知识中,十几种专业类学术杂志更是让他的业余生活无比充实。
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惊艳般的震醒了全世界时,在陈志勇这里却觉得是接上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头——这是他料想到了的结果。所以,对大家称海湾战争为“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的第一场战场”的说法,他有所保留。
陈志勇不喜欢将对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激烈地表现在口头上的辩论。修雷达出身的训练让他认定一个道理: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比设想和预言强。
当时边境还在轮战。每每轮战部队来之前,都要派人先来熟悉熟悉战场环境,向老部队取取经之类的。一次,轮战部队又到军里来取经,其一行人员中有位年轻军官是高炮专业毕业的研究生,这在当时确实算得上凤毛麟角,所以言谈间,他难免有点自视甚高,好像他不是来取经而是来传经的。人又来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于是流露出的优越感更加了一等。对于这位年轻人的态度,陈志勇倒无所谓,但对他的学历或者说学问,陈志勇倒是有深厚的兴趣。于是你来我往地交谈起来,谈着谈着,年轻人的姿态越来越平和、越来越放低下来。因为无论谈到什么“三超”技术(超低副瓣、超宽带、超高分辨)、“四抗”技术(抗干扰、抗反雷达导弹、抗隐身、抗低空入侵),还是苏联的“鸡笼”、“狗窝”和美国的AN/FPS-85相控阵雷达,陈志勇都十分了解,甚至具体到很小的细微的技术问题,陈志勇也几乎无死角、无盲区的全知道。最后这位年轻人很真诚地说,真没想到您知道得这么深入、了解得这么前沿。
陈志勇以他一贯的温和笑了笑说,身在边疆就是国境前沿嘛,再说我是修雷达出身的。
另一个寓言,还是关于忠诚和踏实的穿透力。
时间久了,机关和部队,领导和同志都了解了陈志勇,对他的评价也几乎众口一词——素质不错,有能力,心思是放在谋事、干事上的。
时间在过去,当身边这个那个不断地成为这个长那个长时,陈志勇还在当参谋。当然,在机关当参谋并不是不好。毋庸讳言,军人的荣誉里自然包括晋职的奖励——这是承认、是肯定,是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军人能够施展自己军事才华的台阶。当然,陈志勇不是戚戚于此的人,旁观者却有旁观的看法。
有一回,陈志勇的一位同乡用《庄子》里面的典故调侃他:庄子的《人世间》里有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匠石的木匠带着徒弟出门,看到一棵很大的树被人们当成神明供着,徒弟就说,这棵大树砍了当木料不好吗?匠石观察了一下说,算了吧,这是个散木,什么用都没有,造船会沉、做棺椁会腐烂、打家具不结实。晚上,这棵树就给匠石托梦:你说我没用无才,但你却看看那些有用的树,要么被剥皮折枝,要么早早就被砍了做这样做那样,都“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而我在此地存活了千年,受人膜拜,怎么又不是“以不才而尽享天年”?这位同乡沿着这个故事说,人也是这个道理,能者多劳,却不一定多得。很多能人往往会因为在这个岗位能干而太合适、离不了,而被“需要”,而被耽误掉。
陈志勇置之一笑。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庄子式的诡辩题材。才与不才可以有很多个角度解读,得与失更是如此。所以,不如守中。
事实证明陈志勇的定位是正确的。
一九九六年三月,他由集团军参谋直接升任高炮团团长。

 Post By:2013/4/2 14:42:12
Post By:2013/4/2 14:42:12


 Post By:2013/4/2 15:04:14
Post By:2013/4/2 15:04:14


 Post By:2013/4/2 15:05:35
Post By:2013/4/2 15:05:35


 Post By:2013/4/2 15:06:33
Post By:2013/4/2 15:06:33


 Post By:2013/4/2 15:06:48
Post By:2013/4/2 15:06:48


 Post By:2013/4/2 17:02:03
Post By:2013/4/2 17:02:03




 Post By:2013/4/2 17:47:18
Post By:2013/4/2 17:47:18




 Post By:2013/4/2 18:50:24
Post By:2013/4/2 18:50:24




 Post By:2013/4/2 20:39:14
Post By:2013/4/2 20:3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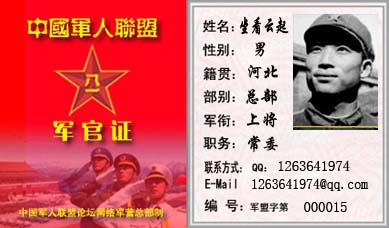


 Post By:2013/4/2 21:02:23
Post By:2013/4/2 21:0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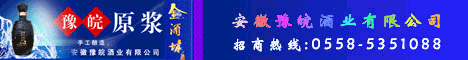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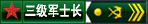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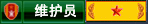







 好文章,阅读了。
好文章,阅读了。


